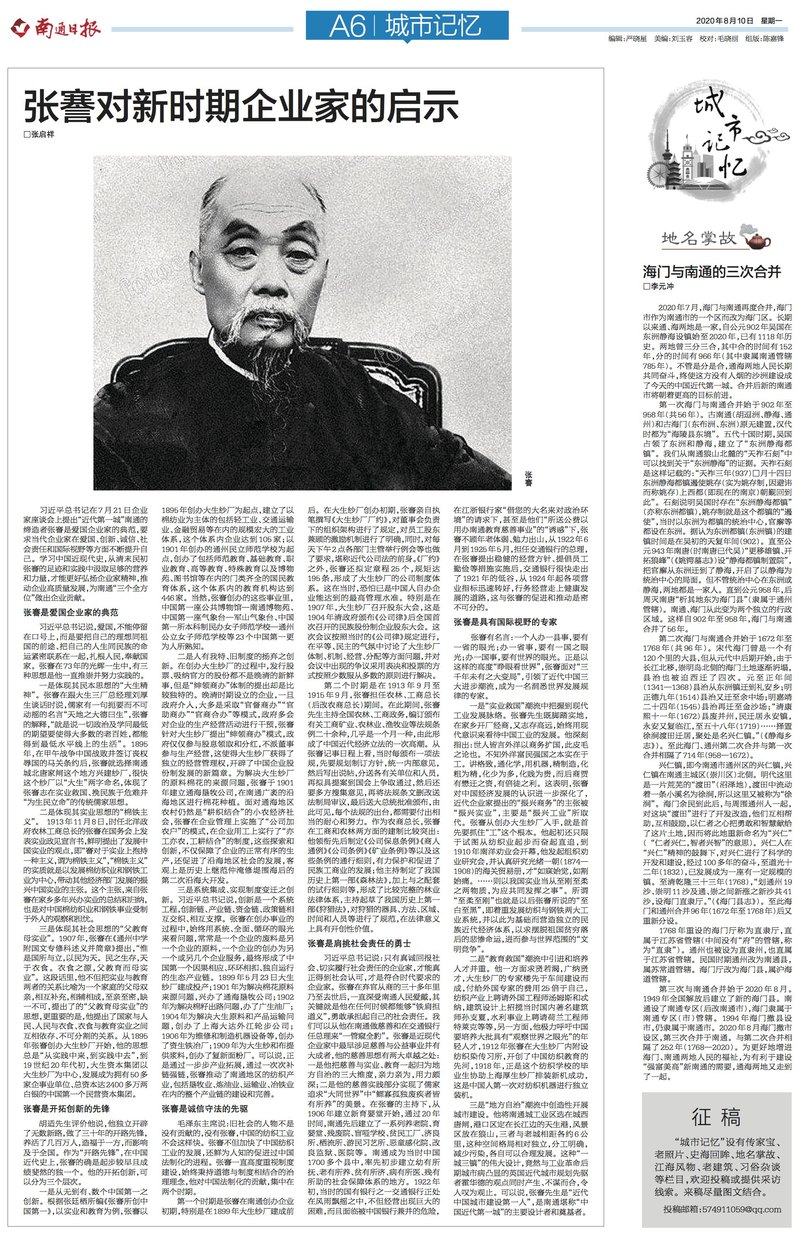
张謇对新时期企业家的启示
江苏大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张启祥
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1日企业家座谈会上提出“近代第一城”南通的缔造者张謇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要求当代企业家在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方面不断提升自己。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从清末民初张謇的足迹和实践中汲取足够的营养和力量,才能更好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为南通“三个全方位”做出企业贡献。
张謇是爱国企业家的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说,爱国,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扎根人民,奉献国家。张謇在73年的光辉一生中,有三种思想是他一直推崇并努力实践的。
一是体现其民本思想的“大生精神”。张謇在跟大生三厂总经理刘厚生谈话时说,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张謇就选择南通城北唐家闸这个地方兴建纱厂,很快这个纱厂以“大生”两字命名,体现了张謇志在实业救国、挽民族于危难并“为生民立命”的传统儒家思想。
二是体现其实业思想的“棉铁主义”。 1913年11月8日,时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的张謇在国务会上发表实业政见宣言书,鲜明提出了发展中国实业的观点,即“謇对于实业上抱持一种主义,谓为棉铁主义”,“棉铁主义”的实质就是以发展棉纺织业和钢铁工业为中心,带动其他经济部门发展的振兴中国实业的主张。这个主张,来自张謇在家乡多年兴办实业的总结和归纳,也是对中国棉纺织业和钢铁事业受制于外人的观察和担忧。
三是体现其社会思想的“父教育母实业”。1907年,张謇在《通州中学附国文专修科述义并简章》提出,“惟是国所与立,以民为天。民之生存,天于衣食。衣食之源,父教育而母实业”。这段话里,他不但把实业与教育两者的关系比喻为一个家庭的父母双亲,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至亲至密,缺一不可,提出了的“父教育母实业”的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国家与人民、人民与衣食、衣食与教育实业之间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从1895年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开始,他的思想总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到19世纪20年代初,大生资本集团以大生纱厂为中心,发展成为拥有50多家企事业单位、总资本达2400多万两白银的中国第一个民营资本集团。
张謇是开拓创新的先锋
胡适先生评价他说,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作为“开路先锋”,在中国近代史上,张謇的确是起步较早且成绩斐然的独一个。他的开拓创新,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一是从无到有、数个中国第一之创新。根据张廷栖所编《张謇所创中国第一》,以实业和教育为例,张謇以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为起点,建立了以棉纺业为主体的包括轻工业、交通运输业、金融贸易等在内的规模宏大的工业体系,这个体系内企业达到105家;以1901年创办的通州民立师范学校为起点,创办了包括师范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特殊教育以及博物苑、图书馆等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国民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内的教育机构达到446家。当然,张謇创办的这些事业里,中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南通博物苑、中国第一座气象台—军山气象台、中国第一所本科制民办女子师范学校—通州公立女子师范学校等23个中国第一更为人所熟知。
二是人有我特、旧制度的扬弃之创新。在创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发行股票、吸纳官方的股份都不是晚清的新鲜事,但是“绅领商办”体制的提出却是比较独特的。晚清时期设立的企业,一旦政府介入,大多是采取“官督商办”“官助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政府多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干预,张謇针对大生纱厂提出“绅领商办”模式,政府仅仅参与股息领取和分红,不派董事参与生产经营,这使得大生纱厂获得了独立的经营管理权,开辟了中国企业股份制发展的新篇章。为解决大生纱厂的原料棉花的来源问题,张謇于1901年建立通海垦牧公司,在南通广袤的沿海地区进行棉花种植。面对通海地区农村仍然是“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社会,张謇在企业管理上实施了“公司加农户”的模式,在企业用工上实行了“亦工亦农,工耕结合”的制度,这些探索和创新,不仅保障了企业的正常有序的生产,还促进了沿海地区社会的发展,客观上是历史上继范仲淹修堤围海后的第二次沿海大开发。
三是系统集成、实现制度变迁之创新。习近平总书记说,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张謇在创办事业的过程中,始终用系统、全面、循环的眼光来看问题,常常是一个企业的废料是另一个企业的原料,一个企业的创办为另一个或另几个企业服务,最终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因果相应、环环相扣、独自运行的生态产业链。1899年5月23日大生纱厂建成投产;1901年为解决棉花原料来源问题,兴办了通海垦牧公司;1902年为解决棉籽出路问题,办了广生油厂;1904年为解决大生原料和产品运输问题,创办了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1906年为维修和制造机器设备等,创办了资生铁冶厂;1909年为大生纱和布提供浆料,创办了复新面粉厂。可以说,正是通过一步步产业拓展,通过一次次补链强链,张謇推动了南通地区的纺织产业,包括垦牧业、炼油业、运输业、冶铁业在内的整个产业链的建设和完善。
张謇是诚信守法的先驱
毛泽东主席说:旧社会的人物不是没有贡献的,没有张謇,中国的纺织工业不会这样快。张謇不但加快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还鲜为人知的促进过中国法制化的进程。张謇一直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始终秉持道德与制度相结合的治理理念,他对中国法制化的贡献,集中在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张謇在南通创办企业初期,特别是在1899年大生纱厂建成前后。在大生纱厂创办初期,张謇亲自执笔撰写《大生纱厂厂约》,对董事会负责下的组织架构进行了规定,对员工股东兼顾的激励机制进行了明确,同时,对每天下午2点各部门主管举行例会等也做了要求,堪称近代公司法的前身。《厂约》之外,张謇还拟定章程25个,规矩达195条,形成了大生纱厂的公司制度体系。这在当时,恐怕已是中国人自办企业能达到的最高管理水准。特别是在1907年,大生纱厂召开股东大会,这是1904年清政府颁布《公司律》后全国首次召开的民族股份制企业股东大会。这次会议按照当时的《公司律》规定进行,在平等、民主的气氛中讨论了大生纱厂体制、机制、经营、分配等方面问题,并对会议中出现的争议采用表决和投票的方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解决。
第二个时期是在1913年9月至1915年9月,张謇担任农林、工商总长(后改农商总长)期间。在此期间,张謇先生主持全国农林、工商政务,编订颁布有关工商矿业、农林业、渔牧业等法规条例二十余种,几乎是一个月一种,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经济立法的一次高潮。从张謇记事日程上看,当时每颁布一项法规,先要规划制订方针,统一内部意见,然后写出说帖,分送各有关单位和人员,再拟具提案到国会上争取通过,然后还要多方搜集意见,再将法规条文删改送法制局审议,最后送大总统批准颁布,由此可见,每个法规的出台,都需要付出相当的耐心和努力。作为农商总长,张謇在工商和农林两方面的建制比较突出:他领衔先后制定《公司保息条例》《商人通例》《公司条例》《矿业条例》等以及这些条例的通行细则,有力保护和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他主持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森林法》,加上与之配套的试行细则等,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林业法律体系,主持起草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狩猎法》,对狩猎的器具、方法、区域、时间和人员等进行了规范,在法律意义上具有开创性价值。
张謇是肩挑社会责任的勇士
习近平总书记说:只有真诚回报社会、切实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才能真正得到社会认可,才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企业家。张謇在弃官从商的三十多年里乃至去世后,一直深受南通人民爱戴,其关键就是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够“铁肩担道义”,勇敢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可以从他在南通做慈善和在交通银行任总理来“一管窥全豹”。张謇是近现代企业家中最早涉足慈善与公益事业并有大成者,他的慈善思想有两大卓越之处:一是他把慈善与实业、教育一起归为地方自治的三大维度,亲力亲为,用力颇深;二是他的慈善实践部分实现了儒家追求“大同世界”中“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美景。在张謇的主持下,从1906年建立新育婴堂开始,通过20年时间,南通先后建立了一系列养老院、育婴堂、残废院、盲哑学校、贫民工厂、济良所、栖流所、游民习艺所、恶童感化院、改良监狱、医院等。南通成为当时中国1700多个县中,率先初步建立幼有所抚、老有所养、贫有所济、病有所医、残有所助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地方。1922年初,当时的国有银行之一交通银行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不但经营出现巨大的困难,而且面临被中国银行兼并的危险,在江浙银行家“借您的大名来对政治环境”的请求下,甚至是他们“所送公费以用办南通教育慈善事业”的“诱惑”下,张謇不顾年老体弱、勉力出山,从1922年6月到1925年5月,担任交通银行的总理,在张謇提出稳健的经营方针、提倡员工勤俭等措施实施后,交通银行很快走出了1921年的低谷,从1924年起各项营业指标迅速转好,行务经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与张謇的促进和推动是密不可分的。
张謇是具有国际视野的专家
张謇有名言:一个人办一县事,要有一省的眼光;办一省事,要有一国之眼光;办一国事,要有世界的眼光。正是以这样的高度“睁眼看世界”,张謇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引领了近代中国三大进步潮流,成为一名洞悉世界发展规律的专家。
一是“实业救国”潮流中把握到现代工业发展脉络。张謇先生既脚踏实地,在家乡开厂经商,又志存高远,始终用现代意识来看待中国工业的发展。他深刻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扩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徒之利。这表明,张謇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近代企业家提出的“振兴商务”的主张被“振兴实业”,主要是“振兴工业”所取代。张謇从创办大生纱厂入手,就是首先要抓住“工”这个根本。他起初还只限于试图从纺织业起步而奋起直追,到1910年南洋劝业会开幕,他发起组织劝业研究会,并认真研究光绪一朝(1874—1908)的海关贸易册,才“如寐始觉,如割始痛。……则以我国实业当从至刚至柔之两物质,为应共同发挥之事”。所谓“至柔至刚”也就是以后张謇所说的“至白至黑”,即着重发展纺织与钢铁两大工业系统,并以此为基础而营造独立的民族近代经济体系,以求摆脱祖国贫穷落后的悲惨命运,进而参与世界范围的“文明竞争”。
二是“教育救国”潮流中引进和培养人才并重。他一方面求贤若渴,广纳贤才,大生纱厂的专家楼先于车间建设而成,付给外国专家的费用25倍于自己,纺织产业上聘请外国工程师汤姆斯和忒纳,建筑设计上招揽当时国内著名建筑师孙支夏,水利事业上聘请荷兰工程师特莱克等等,另一方面,他极力呼吁中国要培养大批具有“观察世界之眼光”的年轻人才,1912年张謇在大生纱厂内附设纺织染传习所,开创了中国纺织教育的先河,1918年,正是这个纺织学校的毕业生协助上海厚生纱厂排装新机成功,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对纺织机器进行独立装机。
三是“地方自治”潮流中创造性开展城市建设。他将南通城工业区选在城西唐闸,港口区定在长江边的天生港,风景区放在狼山,三者与老城相距各约6公里,这种空间格局相对独立,分工明确,减少污染,各自可以合理发展。这种“一城三镇”的伟大设计,竟然与工业革命后期城市病凸显的英国近代城市规划先驱者霍华德的观点同时产生、不谋而合,令人叹为观止。可以说,张謇先生是“近代中国城市建设第一人”,是南通堪称“中国近代第一城”的主要设计者和奠基者。
